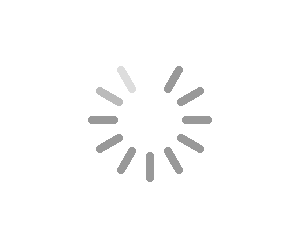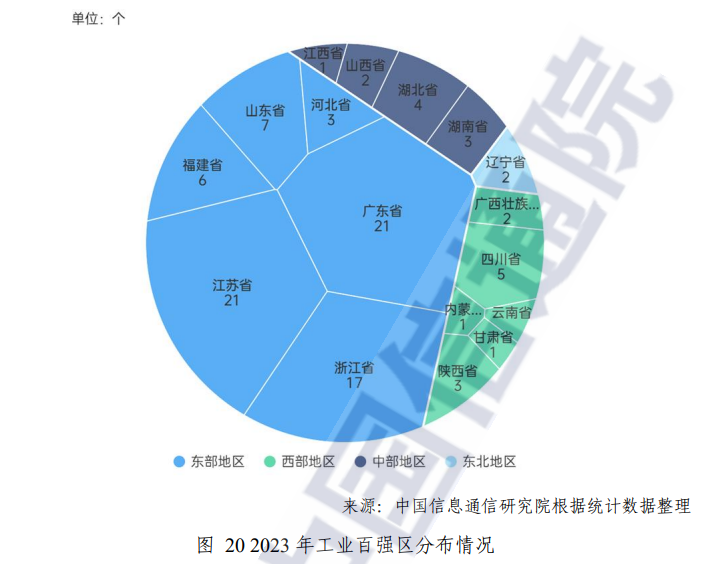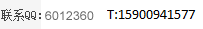车里正在放抖音上流行的《狂浪》:“狂浪是一种态度,狂浪是不被约束,狂浪,狂浪……”我放好行李,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隔壁座的小朋友正在兴高采烈地跟唱“恐龙扛狼恐龙扛”,我想告诉小朋友,这跟车里放的其实是两首歌,但最后只冲他笑了笑。
汽车行进了大概20分钟,窗外开始飞速掠过连绵起伏的群山,司机师傅关掉了音乐,车内突然变得格外安静。小朋友伏在妈妈身上睡着了,没多久,后座也传来呼噜声。我戴上耳机,随机播放音乐,耳机在那一刻仿佛有了自主意识,跳转至郭龙和张玮玮唱的《两个兄弟》——“两个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,坐在星期一的硬座车厢里,这是一辆即将迷途的列车,从下着大雪的石头城里开出来。弟弟说,哥哥你看,我们像不像是断了线的风筝。”
在白银期间,我随李大伟去了一趟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深部铜矿。行进在去深部铜矿的路上,风景变得越发荒诞起来,甚至连偶尔经过的矿工,都如游戏中的NPC,谜一般沉默地走过。偶尔还会有火车开过,广播里发出“嘀嘀嘀,火车来了,车辆行人请注意”的警告声。随后,火车拉着铅锭,蒸汽机车上冒着烟,轰隆隆开过。
白银曾经是铜冶炼的翘楚。图为2013年的白银深部铜矿车站,班车车头在变道。(图/李大伟)
张玮玮曾在歌中将白银称为“下着大雪的石头城”,他说:“人人都在各自的道路上走得无比矫健,充满了《地下》和《黑猫白猫》里的气氛。”
事实的确如此。在去深部铜矿的路上,这样的感受尤为明显。地面上起了碱,矮山上有含铜硫化物经过的痕迹,真的很难不联想到月球,仿佛眼前随时会冒出一个国际空间站,或者如动画片《瑞克和莫蒂》一般,瑞克和莫蒂祖孙二人,正从传送门的另一端通往这里的某片空地。周遭异常安静,只有呼啸的风声。路旁有很多漂亮的红色果子,我咬开尝了尝,味道不错。
李大伟小时候曾因为“小升初”成绩不错,被爸妈奖励了一次暑期旅游。那一次,他们一家三口逛了12个城市,玩了好大一圈。李大伟在北京爬上了长城,买了一件T恤,上面写着“我登上了长城”。一家人合了很多影,笑得特别开心。回来之后,爸妈问他喜不喜欢外面、向不向往大城市,李大伟想了想,说:“我还是喜欢西北。”
早些年,李大伟的父亲因病过世,母亲一个人独自生活。在我去探访的那段时间,李大伟的母亲刚因意外摔坏了腿。李大伟从兰州赶回白银照顾母亲,带她去医院复查,换着花样给她做饭。房间里挂着很多“小蝴蝶”,贴着很多蝴蝶贴画,都是母亲买来装饰用的,她喜欢蝴蝶。我一进门,李大伟就拿出十几本相册,无比热情地过往经历,仿佛把自己视作一杯酒,“哔”一声,把自己和父辈的一生倒在我面前。
郭龙也是这样,和他聊天完全不担心会冷场,他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白银的过往,略带唏嘘且真诚地在白银度过的青春。他身上有音乐人的浪漫和敏感,更有西北人的热情和豪迈。我想,这才是白银人性格的底色。
在白银停留那几天,我去逛了金鱼公园,公园里有好大一片人工湖,还有很多枝叶茂盛、高高大大的树。那几天天气很好,湛蓝的天空下,云朵仿佛近在咫尺,硕大、松软、雪白,和人一起散步。
郭龙时常会想起金鱼公园,那感觉仿佛就在昨日——“我们那边没什么水,很干旱,能在市区建一个人工湖,真的太棒了。小时候,我们带上一瓶橘子汽水、拿上一块面包,能在人工湖旁边玩一天。有时铺一个塑料垫子,再带上点水果,就当作野餐了。”
郭龙还记得白银的云,那些似乎没什么边界感,总是离人很近的大坨大坨的漂亮的云,就这么一直飘在他记忆的最深处。
小学六年级,郭龙下午4点多就放学了。父母还在单位上班,他就和小伙伴跑到铁路边,顺着铁轨一直走,走累了,就在附近找个小山坡躺下,躺在太阳晒过的草地上,盯着天上的云看。“那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啊,有好多奢望,想爱,想吃,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一眨眼,人生就这样过去了。”
2023年9月,张玮玮发布了一张名为《沙木黎》的新专辑,主打歌里合成器丰富的音色,让人仿佛置身于广袤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之中。郭龙最喜欢专辑里的《永丰街》,歌里唱道:“你躺在太阳晒过的枕木上,我在星期二的下午,什么都不知道。生锈的铁门,在风中摇晃,你在地平线上越来越远。从银河系看过来,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分开,从我这里看过去,你比银河系还遥远。”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,首发于新周刊652期,作者:傅淼淼,运营:李靖越,监制:罗屿
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虎嗅立场。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授权事宜请联系hezuo@huxiu.com如对本稿件有异议或投诉,请联系tougao@huxiu.co
文章来源于:http://www.wmaa.cn 城市网
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,其真实性与本站无关,请网友慎重判断